长江、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,并没有到唐古拉山去寻源拜神,中国人对山岳的崇拜,来自“万物有灵”的自然观。
从“禹封九顶”算起,祭祀山神的圣典,在中国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。《礼记·祭法》:山林川谷丘陵,能出云、为风雨、见怪物,皆曰神。
至于那些高入霄汉,形象奇特,难以攀登的险峻山岳,更认为是通天之处,为神灵仙人所居。《山海经》上说:“昆仑之丘,实惟帝之下都。”他们认为那最高的昆仑山,‘是天帝在地上的都城。
从孔子的“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”到秦汉时代的“自然比德”,则来源于更深层的“天人合一”意识。人与天地结构是一体化的:天有九野,地有九州,人有九窍;宇宙有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,人有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;自然有五岳,社会有五帝,五方神抵,人有仁、义、礼、智、’信五德……这种“天人合一”观念,分明把人的感情、意志、伦理透射在外部世界,自然山水打上了人文精神的印记。
汉代阴阳五行说,则直接导致中国特有的“风水论”:气乘风则散,界水则止,古人聚之使不散,行之使有止,故谓之风水。(晋郭璞《葬经》)
“风水论”用抽象的气来解释自然环境。按照气的运动变化规律,阴阳两气交流而生出各种变化,浊者沉为地,清者浮为天。山高而巍峨者,称为“后龙”,后龙之后的山脉称为“来龙”或“祖山”,祖山必绵绵婉蜒,方显生气勃勃。左右宜有小山护卫合抱,称“龙砂”。这样的山势环境,才有天地氰员之气往来。“后龙”正面还要有远山对景,称为“案山”或“朝山”。山峦叠嶂,“负阴抱阳”,草木方显旺盛,乃为“瑞气葱茏”的徵兆。所以“仙山”、“佛国”常建在这些山势奇特、林深木茂之处,因是神仙佛祖所居之圣地,自然被称为“风水宝地”。
魏晋以来,佛教兴盛。由于文人与僧人交游往来,而寺院又往往成为文人政治避难的世外桃园。魏晋文人寄情畅神于自然山水,不仅找到“山水以形媚道”老庄玄学表达的最佳方式,而且发现了山水的自然美。因此多把庄园与寺院建在幽静的山林之中,既可以全身远祸,过一种闲云野鹤般的、适意会少的生活,又可以超脱“红尘”,有利于文人“澄怀观道”,甚至还包括希冀延年益寿的生理需求在内。
唐以后的禅宗,改变了早期佛教持钵行乞的苦行僧的生活方式,更讲究人与自然的融合关系。禅师们常常沉浸在青山白云、流水清泉之中,领悟生命的真话。深山里的古刹,常常是禅师们悟道之所;丛林禅院,成为僧人们参禅打坐的清净之地。而那些朝圣者的足迹,常在遥远的青山岭外,白云深处,在一路的山重水复之中,攀上那岭头金顶,才恍然大悟,顿见本来面目。

丛林建筑选址的精心,包含着从观念到实体建筑的佛家原理:第一,利于修道。佛教认为,修行的第一要素即是割断尘缘,与世无染。释迦修道之初,在菩提树下结跏趺坐,在野鹿苑说法;达摩一苇渡江,见高山秀丽,遂居而悟禅;慧理至杭,见飞来峰颇似印度灵鹫峰,乃筑室而居。可见佛徒皆效法佛祖,丛林建筑多选佳丽之地,于是代代相传,遂成定制。第二,利于广召信徒。游人入寺观光,信徒入寺降香,佛殿肃穆庄严,钟磬贯耳。当人们置身于丛林所掩映的梵宫佛寺中时,与宗教净化意识并生的是身清气洁的审美感受。幽深的丛林与净土世界似乎更有环境、氛围的暗合之处。所以僧家占尽湖光山景,是一种包含宗教目的的选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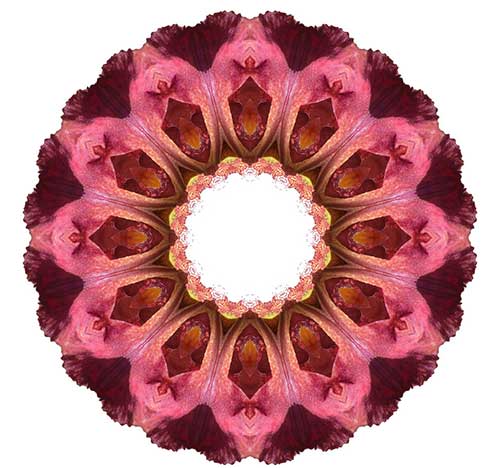
传入中国的佛教,显然已经淡化印度人那种狂热而痴迷的神山朝拜意识,而把宗教的修炼化为一种生活的情趣,一种审美的意念,甚至包括上述深层意识下形成的中国特有的风水之论。这也许就是历代佛教要把寺院多建在深山幽林的深层的历史原因吧。